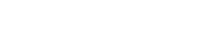“木家婶子,按理儿说我也不该在这当口来,可你们家老木也走了这么些天了,当初下葬的时候,我们家那口子该出力的时候可一点没含糊,就老木被拉回来的时候吧,还是我们家那口子花钱雇得牛车吧。”烈日炎炎下,一个膀大腰圆地壮实妇人双手叉着腰站在木家院门前,天生的大嗓门引得街坊四邻的闲人都凑到了木家门前。
妇人着一身糙衣,裤腿高高卷起,露出两只沾着泥的粗壮脚丫子。
木家屋门前,木家的寡妇孙画儿双手紧紧搂着一个瘦小枯黄的男娃,一声不吭。
“周婶子,这是出啥子事了?”从围观的闲人里窜出一个尖脸刻薄相的小妇人,凑到那壮实妇人身边问了一句。
“还不是那日拉她们家老木回来的牛车费,那一趟包车还拉了死人,车夫可不愿哩,还是我们家那口子出了二十文,那牛车的车夫才愿意拉人回来哩。”周婶子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脸上愈发地不耐烦了,语气也更冲了。
“周家婶子,老木家的瞧着也不容易,一个痴傻儿,还有一个不开窍的丫头,那丫头昨日里还为了捉鱼落到了村口那条河里,到现在只怕还没醒呢!现在老木家家里实顶实得怕是也揭不开锅了。”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一个闲汉嘴角嚼着一根枯草,替屋内局促的木家媳妇儿孙画儿开口道。
周婶子听了,嗤声一笑,张口便道:“老王家的,你不是瞧上了木婶子吧?老木家的可才刚死,指不定还要回门看看呢,就看你有没有这胆儿了!”
“你……你……你胡说!”孙画儿被气得不轻,一张俏丽白皙的脸颊被涨得通红。
“我胡说?”周婶子笑得更大声了,“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木家婶子,你要是心里头真亮亮堂堂的,干甚子不将我们家老周的二十文还来!难不成是惦记着我们家老周?我们家老周没个心眼的,老娘我可不是吃素的!”
说着,那周婶子又撸了撸袖子,“我们家迅哥儿马上可就要上学堂了,这学堂的学费还没个着落呢!木家婶子,你若是识相点的,就早点将银子拿出来,不然我也只能自己进去拿了。”
孙画儿眼眶通红,低声下气地恳求道:“周婶,能不能……再宽限两日,矜矜她还发着烧,我……我想给矜矜抓药。”
“你真当你家傻丫头是个宝呢?我家讯哥儿可年年得学堂里先生的夸呢!你家痴儿傻女的,发烧揪一把艾草嚯嚯,一碗水就退了,还抓药哩!又不是城里的金贵小姐,没那个命!”周婶子毫不客气的讽刺道。
话音落地,周婶子也懒得再同孙画儿叨咕,直接抬了脚便要进屋。
孙画儿连眼角的泪都来不及拭去,忙伸手便要拦去,“矜矜还在睡着,矜矜……”
周婶子右手轻轻一推,孙画儿连带着怀里搂着的孩子一并倒在了地上。
“装什么呢?”周婶子嫌弃地朝着地上啐了一口,压低了声音道:“我呸,刚死了男人就开始勾引男人的骚贱蹄子!”
“你哪一只眼睛看到我娘勾引男人了?”一声犹如地府索命般地冷厉讽笑传出,周婶子光着的小腿陡然升起一丝寒意,她颤颤地抬了抬脑袋。
恰好看到屋内的一张破旧的桌前,一个瘦弱却精练的女子一脚踩在长凳上,骨瘦如柴的右手抵着大腿,指尖轻轻转着一把尖利的剪刀。
妇人着一身糙衣,裤腿高高卷起,露出两只沾着泥的粗壮脚丫子。
木家屋门前,木家的寡妇孙画儿双手紧紧搂着一个瘦小枯黄的男娃,一声不吭。
“周婶子,这是出啥子事了?”从围观的闲人里窜出一个尖脸刻薄相的小妇人,凑到那壮实妇人身边问了一句。
“还不是那日拉她们家老木回来的牛车费,那一趟包车还拉了死人,车夫可不愿哩,还是我们家那口子出了二十文,那牛车的车夫才愿意拉人回来哩。”周婶子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脸上愈发地不耐烦了,语气也更冲了。
“周家婶子,老木家的瞧着也不容易,一个痴傻儿,还有一个不开窍的丫头,那丫头昨日里还为了捉鱼落到了村口那条河里,到现在只怕还没醒呢!现在老木家家里实顶实得怕是也揭不开锅了。”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一个闲汉嘴角嚼着一根枯草,替屋内局促的木家媳妇儿孙画儿开口道。
周婶子听了,嗤声一笑,张口便道:“老王家的,你不是瞧上了木婶子吧?老木家的可才刚死,指不定还要回门看看呢,就看你有没有这胆儿了!”
“你……你……你胡说!”孙画儿被气得不轻,一张俏丽白皙的脸颊被涨得通红。
“我胡说?”周婶子笑得更大声了,“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木家婶子,你要是心里头真亮亮堂堂的,干甚子不将我们家老周的二十文还来!难不成是惦记着我们家老周?我们家老周没个心眼的,老娘我可不是吃素的!”
说着,那周婶子又撸了撸袖子,“我们家迅哥儿马上可就要上学堂了,这学堂的学费还没个着落呢!木家婶子,你若是识相点的,就早点将银子拿出来,不然我也只能自己进去拿了。”
孙画儿眼眶通红,低声下气地恳求道:“周婶,能不能……再宽限两日,矜矜她还发着烧,我……我想给矜矜抓药。”
“你真当你家傻丫头是个宝呢?我家讯哥儿可年年得学堂里先生的夸呢!你家痴儿傻女的,发烧揪一把艾草嚯嚯,一碗水就退了,还抓药哩!又不是城里的金贵小姐,没那个命!”周婶子毫不客气的讽刺道。
话音落地,周婶子也懒得再同孙画儿叨咕,直接抬了脚便要进屋。
孙画儿连眼角的泪都来不及拭去,忙伸手便要拦去,“矜矜还在睡着,矜矜……”
周婶子右手轻轻一推,孙画儿连带着怀里搂着的孩子一并倒在了地上。
“装什么呢?”周婶子嫌弃地朝着地上啐了一口,压低了声音道:“我呸,刚死了男人就开始勾引男人的骚贱蹄子!”
“你哪一只眼睛看到我娘勾引男人了?”一声犹如地府索命般地冷厉讽笑传出,周婶子光着的小腿陡然升起一丝寒意,她颤颤地抬了抬脑袋。
恰好看到屋内的一张破旧的桌前,一个瘦弱却精练的女子一脚踩在长凳上,骨瘦如柴的右手抵着大腿,指尖轻轻转着一把尖利的剪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