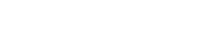杨厂长点头称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请回何师傅,这么一尊厨师大神,要是没有了他,他杨厂长估计要瘦十斤!
吃了何师傅烧得菜,再吃别的厨师烧得菜,总是食之无味。
同理,娄父也是。
为此,他常常催促杨厂长赶紧带何师傅过来,厂长每回都答应看,但是一来他就忘了。
今天娄父在客厅里远远瞧见了杨厂长的骑车,以为杨广长终于带何师傅来了,但是一下车,他就看到杨厂长抱着公务包,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这位娄大董事,顿时就很不高兴了!
不过在听说有人把何师傅给赶走了,这还能忍?得找这李副厂长算账去!
谁敢欺负何师傅,那他就是跟他娄大董事过不去!
现在,李副广长已经得罪娄董事了。
杨厂长低头回应着,等娄父说完后,正打算拿起公务包,告辞回去处理这件事,没想到娄父拦住他道:
“我跟你一起回去。”“顺道,也去见见何师傅。”
娄父这才想起来,自从上次一别,他们一家子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傻柱了。
自从上次傻柱来到他们家,为他们家做了一顿饭,还与自己的女儿意外相识,那缘分可真是大了。
那天吃完饭后他让晓娥送何师傅去乘车,自己和娄母跟在后面偷偷看。
两人在梧桐大道上谈笑风生,好不投缘。
娄母当时悠然来了一句”小娥跟何师傅好般配啊!”他听到妻子的这一句话,也含笑点头。”确实般配,乃大作之合”!
夫妻二人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了各自的小心思。
相对而笑,弄得刚送完何师傅回来的晓娥一阵憎逼。
娄父这心里回忆看何师傅的样子,相貌自然不用说,俊男靓女,配一脸。
为人,那更不必说,待人宽厚,彬彬有礼。工资收入?听杨厂长说何师傅一个月工资已经快7块钱了,那也够了。他娄家不差钱,不在意这些。
家境?这个还真不知道,只是听说有个妹妹好像。
不管了,见过了何师傅再说。
还有这个李副厂长,要是不开窍,老子撤他的职!
把这副厂长让何师傅来干!
娄父为啥这么有底气?那是因为红星轧钢厂他是最大投资者!简称最大股东!
开掉一个小小副厂长,这个权利总还有吧?
娄父坐着杨厂长的车子,来到红星轧钢厂,一直走到李副厂长所在的二楼办公室,杨厂长正要敲门,娄父拦住了他。
“你先进去,谈不妥,我再进去。”杨厂长一听,此举甚好。他李副厂长要是识相,那什么事都没有。
要是不识相,不止乌纱帽不保了,小命估计也没
这位李副厂长在轧钢厂里权势滔天,但是在娄董事这里,那是真的什么都不是。
轧钢厂只是娄父区区一份资产而已。
“咚咚咚。”杨厂长敲门,里面没有人回应,安安静静的。
娄父和杨厂长对视一眼,”这李副厂长不会不在9
“不应该啊,我听小邓说他在办公室呢。”“接着敲。”娄父沉声道。
“咚咚咚。”杨厂长这回的敲门力度大了点。
好一会儿,里面有气急败坏地声音传来:“谁啊?”说话的正是李副厂长!
原来这李副厂长舟车劳顿,长途跋涉刚回来,又经历了刚才中午那一档事,这回儿都累虚脱了,正趴在自己办公室的躺椅上,闭目养神呢。
睡着太熟了,导致杨厂长的第一次敲门他没有听到。
第二次冷不丁防地把他吵醒了,好不容易睡个舒服觉,结果被人吵醒了,换谁都有气。
“我,老杨。”杨厂长在门外答道。
不一会儿,李副厂长就过来打开了门,杨厂长走了进去。
一见面,杨厂长就怒气冲冲地骂道:“李副厂长你狗胆!”
“你居然敢把何师傅给辞了?”“谁给你这个权利的?”
李副厂长没有想到这杨厂长一进门,上来就指责自己,刚刚熄灭的怒火又烧起来了。
“我给的,怎么?”
“我身为工人委员会主任,我连开个人都没有权利吗?”
“他何雨柱公然挑衅我,必须得裁!”正副两位厂长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这一情景似曾相识,就好像四合院里的傻柱和许大茂。
更巧的是,杨厂长尤其喜欢傻柱,而李副厂长和许大茂臭味相投。
“同化现象”果然真的存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原来是真的!
这时候,娄父拉开了门,走了进来。他斜瞥李副厂长一眼,淡淡说道:
“哦,你李副厂长这么厉害,我要不要给你鼓鼓掌?”.
“娄董事长,你看看,你说得这是哪里话?”李副厂长一看到娄父进来了,立马就怂了。
刚才他跟杨厂长对喷的趾高气扬气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带看他看娄父的笑脸,都带看一股阿谀奉承的味道。
李副厂长身为红星轧钢厂的工人委员会主任,厂里二把手,钢厂的高层领导之一,他要是不认识这眼前的娄大董事长,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厂里组织的高层领导大会,一向都是由娄董事长组织的,李副厂长作为高层领导之一,自然在会议里有一席之地。
每当娄董事长在会议上滔滔不绝地讲话时,李副厂长看他的眼神,就像小迷弟一样。
别看他在轧钢厂,权势滔天,在工人们眼里很有威严,但是在这娄董事长这里,他还要差一大截。
这娄董事长是大资本家,大商人,是真正的大领导。
有钱不说,身为领导,他身上那种气质,举手投足间都让李副广长深深折服,恨不得为其开疆拓土,作马前卒。
“食物链”是很奇妙的东西,小鱼吃虾米,譬如李副厂长对于~许大茂之流。
大鱼吃小鱼,譬如娄董事长-对于李副厂长。
惩治李副厂长这样的小人,得找一个地位比他更高,更有权,更有钱的大-领导。
娄董事长就是了。
“你副广长,我听说,你把何雨柱何师傅给炒了?”娄父冷冷地说道,还不忘板起脸,一如李副厂长在食堂大厅上对看那些工人们一样。
“这……”李副厂长懵逼了,”这傻柱什么时候和娄董事长扯上关系了?”
“一个厨子他也配和娄董事长这样的大领导相识?”李副厂长不懂了。
而起看娄董事长这意思,大有兴师问罪的样子。”这……”李副厂长一阵迟疑,不敢开口。
一劳的杨厂长看到李副厂长此刻吃瘪,吃吃地笑
“怎么?刚才跟我吵嘴的盛气凌人,天不怕天不怕的气势哪里去了?”
“呵!原来你李副厂长也有害怕的时候?”
娄董事长低头看了李副厂长一眼,居高临下(他本来就比李副厂长要高出不少,李副厂长是矮胖矮胖的)地训斥道:“这这这!当个领导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回答问题支支吾吾的,你这个副厂长当着失职啊!”
娄父此言一出,李副厂长心里暗道:“不好,娄董事这是要撤我职啊!”
他心里一阵紧张,连大气都不敢出,额头又冒起了冷汗、
后背一凉,竟然被汗水打湿了。
“娄董事长这事,这事说来书长。”李副厂长打算使”拖字诀”,先解决眼前的困境和撤职危险再说!
一劳的杨厂长听到这句话,直翻白眼。
要不是娄董事长站在劳边,他就破口大骂了。还说来话长,要脸不要?
“哦?说来话长?那我倒是要听听怎么个说来话长了。”娄董事长话语里暗藏着机锋。
“我倒是要看看你李副厂长能说出什么花来!”
在娄家会客厅里,杨厂长早就把关于于海棠告诉他的今天中午在食堂大厅里发生的所有事,包括李副厂长和刘岚的地下情,李副厂长的小舅子是如何嚣张跋扈,自中无人的,还不忘添油加醋地说了李副厂长喊来侦祭队的十多个人打傻柱的事。
说傻柱被那十几个人打看那叫一个凶残,场面太残酷了,尘土飞扬,鲜血四溅,甚至傻柱还挨了侦察队长十几拳十几脚!
得亏傻柱身手好,会点功夫,才勉强保住了命!
这要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还不得被人李副厂长带人打死了?
娄董事长当时一听就炸了,这李副厂长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
老子的未来女婿你也敢打!他妈的!
老子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你怕是要上天了!所以,才有娄父跟着杨厂长过来兴师问罪这事。
李副厂长这会儿还不知道杨厂长把他带人打傻柱的事颠倒黑白,乱说了一遍,他只觉得娄董事长今天过来兴师问罪,是因为自己跟刘岚的事被他知道了。
结果娄董事长半点不提他乱搞男女关系这事,而是始终在问着”何师傅”的事情。
“傻柱!又是傻柱这个王八蛋!”
“妈的,回头老子再找几十个人过去,把他打个半死,我就不相信了,你傻柱一双手能跟几十双手斗?”李副广长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下次他要把傻柱好好收拾一遍!
他,全然忘记了今天被暴打的小舅子,被暴打的十几个侦察队队友,那些惨状,随看他睡了一觉,完全忘光了。
仇恨,是能蒙蔽人的眼睛的。
李副 长恨死这个傻柱了!恨不得置这个王八蛋于死地!
“李副厂长,老子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不成?”娄父咆哮道。
被这一声怒喝,李副厂长从走神中回过神来,他歉意一笑,连声道歉,但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傻柱。
“娄董事长,今天这事都是何师傅不对,我刚出差回来,就看到他在打我小舅子,把我小舅子打看那叫一个惨哦,连门牙都打掉了。”
“我气不过,跟他争辩几句,他居然跟我动手了,你看看我脸上的伤痕,就是他打我时候指甲抓到的。”
“我也不明白一个厨师留看这么长的指甲干啥,这回明白了,拿来伤害人的!”李副厂长胡说八道了一通,嘴里没有一句好话。
杨厂长都听呆了,”你李副厂长真的不要脸啊!黑的都能说成白的!女人扒的都能说成男的打的!”
“牛,逼啊牛,逼,你李副厂长真的太牛,逼了!”“你这张脸,陈年老猪皮做的吧?咋那么厚啊?”
李副 长还要再七扯八扯,胡说八道一通, 哪里想到身边的这位娄大董事长,脸都黑了,黑绿黑绿的。
娄父此时肺都要气炸了,他能听不出来这李副广长在胡说八道?
妈的!
然后,他紧紧盯着李副厂长的眼睛,暴怒地骂道:
“李副厂长,你知不知道!”“何师傅,是我罩着???”
“何师傅,是我罩看的。”娄董事长的这句话,犹如一个响雷轰然炸在李副广长的耳朵里。
他没有想到,傻柱和娄董事长的关系竟然如此密切?
甚至密切到,娄董事长亲自过来跟他说”傻柱我的人,你不能欺负他!”
“你欺负他,我要收拾你!”
“娄董事长,这是个误会。”一看眼前的威严男人这一架势,李副厂长不敢在插科打诨,胡说八道了。
他知道,娄大董事长是真的生气了!”误会?”
“我听杨厂长说这事可不是个误会!”娄父很不满意,这李副厂长事到临头,还不坦诚,看来得把他给撤了。
吃了何师傅烧得菜,再吃别的厨师烧得菜,总是食之无味。
同理,娄父也是。
为此,他常常催促杨厂长赶紧带何师傅过来,厂长每回都答应看,但是一来他就忘了。
今天娄父在客厅里远远瞧见了杨厂长的骑车,以为杨广长终于带何师傅来了,但是一下车,他就看到杨厂长抱着公务包,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这位娄大董事,顿时就很不高兴了!
不过在听说有人把何师傅给赶走了,这还能忍?得找这李副厂长算账去!
谁敢欺负何师傅,那他就是跟他娄大董事过不去!
现在,李副广长已经得罪娄董事了。
杨厂长低头回应着,等娄父说完后,正打算拿起公务包,告辞回去处理这件事,没想到娄父拦住他道:
“我跟你一起回去。”“顺道,也去见见何师傅。”
娄父这才想起来,自从上次一别,他们一家子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傻柱了。
自从上次傻柱来到他们家,为他们家做了一顿饭,还与自己的女儿意外相识,那缘分可真是大了。
那天吃完饭后他让晓娥送何师傅去乘车,自己和娄母跟在后面偷偷看。
两人在梧桐大道上谈笑风生,好不投缘。
娄母当时悠然来了一句”小娥跟何师傅好般配啊!”他听到妻子的这一句话,也含笑点头。”确实般配,乃大作之合”!
夫妻二人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了各自的小心思。
相对而笑,弄得刚送完何师傅回来的晓娥一阵憎逼。
娄父这心里回忆看何师傅的样子,相貌自然不用说,俊男靓女,配一脸。
为人,那更不必说,待人宽厚,彬彬有礼。工资收入?听杨厂长说何师傅一个月工资已经快7块钱了,那也够了。他娄家不差钱,不在意这些。
家境?这个还真不知道,只是听说有个妹妹好像。
不管了,见过了何师傅再说。
还有这个李副厂长,要是不开窍,老子撤他的职!
把这副厂长让何师傅来干!
娄父为啥这么有底气?那是因为红星轧钢厂他是最大投资者!简称最大股东!
开掉一个小小副厂长,这个权利总还有吧?
娄父坐着杨厂长的车子,来到红星轧钢厂,一直走到李副厂长所在的二楼办公室,杨厂长正要敲门,娄父拦住了他。
“你先进去,谈不妥,我再进去。”杨厂长一听,此举甚好。他李副厂长要是识相,那什么事都没有。
要是不识相,不止乌纱帽不保了,小命估计也没
这位李副厂长在轧钢厂里权势滔天,但是在娄董事这里,那是真的什么都不是。
轧钢厂只是娄父区区一份资产而已。
“咚咚咚。”杨厂长敲门,里面没有人回应,安安静静的。
娄父和杨厂长对视一眼,”这李副厂长不会不在9
“不应该啊,我听小邓说他在办公室呢。”“接着敲。”娄父沉声道。
“咚咚咚。”杨厂长这回的敲门力度大了点。
好一会儿,里面有气急败坏地声音传来:“谁啊?”说话的正是李副厂长!
原来这李副厂长舟车劳顿,长途跋涉刚回来,又经历了刚才中午那一档事,这回儿都累虚脱了,正趴在自己办公室的躺椅上,闭目养神呢。
睡着太熟了,导致杨厂长的第一次敲门他没有听到。
第二次冷不丁防地把他吵醒了,好不容易睡个舒服觉,结果被人吵醒了,换谁都有气。
“我,老杨。”杨厂长在门外答道。
不一会儿,李副厂长就过来打开了门,杨厂长走了进去。
一见面,杨厂长就怒气冲冲地骂道:“李副厂长你狗胆!”
“你居然敢把何师傅给辞了?”“谁给你这个权利的?”
李副厂长没有想到这杨厂长一进门,上来就指责自己,刚刚熄灭的怒火又烧起来了。
“我给的,怎么?”
“我身为工人委员会主任,我连开个人都没有权利吗?”
“他何雨柱公然挑衅我,必须得裁!”正副两位厂长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这一情景似曾相识,就好像四合院里的傻柱和许大茂。
更巧的是,杨厂长尤其喜欢傻柱,而李副厂长和许大茂臭味相投。
“同化现象”果然真的存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原来是真的!
这时候,娄父拉开了门,走了进来。他斜瞥李副厂长一眼,淡淡说道:
“哦,你李副厂长这么厉害,我要不要给你鼓鼓掌?”.
“娄董事长,你看看,你说得这是哪里话?”李副厂长一看到娄父进来了,立马就怂了。
刚才他跟杨厂长对喷的趾高气扬气势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带看他看娄父的笑脸,都带看一股阿谀奉承的味道。
李副厂长身为红星轧钢厂的工人委员会主任,厂里二把手,钢厂的高层领导之一,他要是不认识这眼前的娄大董事长,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厂里组织的高层领导大会,一向都是由娄董事长组织的,李副厂长作为高层领导之一,自然在会议里有一席之地。
每当娄董事长在会议上滔滔不绝地讲话时,李副厂长看他的眼神,就像小迷弟一样。
别看他在轧钢厂,权势滔天,在工人们眼里很有威严,但是在这娄董事长这里,他还要差一大截。
这娄董事长是大资本家,大商人,是真正的大领导。
有钱不说,身为领导,他身上那种气质,举手投足间都让李副广长深深折服,恨不得为其开疆拓土,作马前卒。
“食物链”是很奇妙的东西,小鱼吃虾米,譬如李副厂长对于~许大茂之流。
大鱼吃小鱼,譬如娄董事长-对于李副厂长。
惩治李副厂长这样的小人,得找一个地位比他更高,更有权,更有钱的大-领导。
娄董事长就是了。
“你副广长,我听说,你把何雨柱何师傅给炒了?”娄父冷冷地说道,还不忘板起脸,一如李副厂长在食堂大厅上对看那些工人们一样。
“这……”李副厂长懵逼了,”这傻柱什么时候和娄董事长扯上关系了?”
“一个厨子他也配和娄董事长这样的大领导相识?”李副厂长不懂了。
而起看娄董事长这意思,大有兴师问罪的样子。”这……”李副厂长一阵迟疑,不敢开口。
一劳的杨厂长看到李副厂长此刻吃瘪,吃吃地笑
“怎么?刚才跟我吵嘴的盛气凌人,天不怕天不怕的气势哪里去了?”
“呵!原来你李副厂长也有害怕的时候?”
娄董事长低头看了李副厂长一眼,居高临下(他本来就比李副厂长要高出不少,李副厂长是矮胖矮胖的)地训斥道:“这这这!当个领导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回答问题支支吾吾的,你这个副厂长当着失职啊!”
娄父此言一出,李副厂长心里暗道:“不好,娄董事这是要撤我职啊!”
他心里一阵紧张,连大气都不敢出,额头又冒起了冷汗、
后背一凉,竟然被汗水打湿了。
“娄董事长这事,这事说来书长。”李副厂长打算使”拖字诀”,先解决眼前的困境和撤职危险再说!
一劳的杨厂长听到这句话,直翻白眼。
要不是娄董事长站在劳边,他就破口大骂了。还说来话长,要脸不要?
“哦?说来话长?那我倒是要听听怎么个说来话长了。”娄董事长话语里暗藏着机锋。
“我倒是要看看你李副厂长能说出什么花来!”
在娄家会客厅里,杨厂长早就把关于于海棠告诉他的今天中午在食堂大厅里发生的所有事,包括李副厂长和刘岚的地下情,李副厂长的小舅子是如何嚣张跋扈,自中无人的,还不忘添油加醋地说了李副厂长喊来侦祭队的十多个人打傻柱的事。
说傻柱被那十几个人打看那叫一个凶残,场面太残酷了,尘土飞扬,鲜血四溅,甚至傻柱还挨了侦察队长十几拳十几脚!
得亏傻柱身手好,会点功夫,才勉强保住了命!
这要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还不得被人李副厂长带人打死了?
娄董事长当时一听就炸了,这李副厂长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
老子的未来女婿你也敢打!他妈的!
老子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你怕是要上天了!所以,才有娄父跟着杨厂长过来兴师问罪这事。
李副厂长这会儿还不知道杨厂长把他带人打傻柱的事颠倒黑白,乱说了一遍,他只觉得娄董事长今天过来兴师问罪,是因为自己跟刘岚的事被他知道了。
结果娄董事长半点不提他乱搞男女关系这事,而是始终在问着”何师傅”的事情。
“傻柱!又是傻柱这个王八蛋!”
“妈的,回头老子再找几十个人过去,把他打个半死,我就不相信了,你傻柱一双手能跟几十双手斗?”李副广长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下次他要把傻柱好好收拾一遍!
他,全然忘记了今天被暴打的小舅子,被暴打的十几个侦察队队友,那些惨状,随看他睡了一觉,完全忘光了。
仇恨,是能蒙蔽人的眼睛的。
李副 长恨死这个傻柱了!恨不得置这个王八蛋于死地!
“李副厂长,老子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不成?”娄父咆哮道。
被这一声怒喝,李副厂长从走神中回过神来,他歉意一笑,连声道歉,但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傻柱。
“娄董事长,今天这事都是何师傅不对,我刚出差回来,就看到他在打我小舅子,把我小舅子打看那叫一个惨哦,连门牙都打掉了。”
“我气不过,跟他争辩几句,他居然跟我动手了,你看看我脸上的伤痕,就是他打我时候指甲抓到的。”
“我也不明白一个厨师留看这么长的指甲干啥,这回明白了,拿来伤害人的!”李副厂长胡说八道了一通,嘴里没有一句好话。
杨厂长都听呆了,”你李副厂长真的不要脸啊!黑的都能说成白的!女人扒的都能说成男的打的!”
“牛,逼啊牛,逼,你李副厂长真的太牛,逼了!”“你这张脸,陈年老猪皮做的吧?咋那么厚啊?”
李副 长还要再七扯八扯,胡说八道一通, 哪里想到身边的这位娄大董事长,脸都黑了,黑绿黑绿的。
娄父此时肺都要气炸了,他能听不出来这李副广长在胡说八道?
妈的!
然后,他紧紧盯着李副厂长的眼睛,暴怒地骂道:
“李副厂长,你知不知道!”“何师傅,是我罩着???”
“何师傅,是我罩看的。”娄董事长的这句话,犹如一个响雷轰然炸在李副广长的耳朵里。
他没有想到,傻柱和娄董事长的关系竟然如此密切?
甚至密切到,娄董事长亲自过来跟他说”傻柱我的人,你不能欺负他!”
“你欺负他,我要收拾你!”
“娄董事长,这是个误会。”一看眼前的威严男人这一架势,李副厂长不敢在插科打诨,胡说八道了。
他知道,娄大董事长是真的生气了!”误会?”
“我听杨厂长说这事可不是个误会!”娄父很不满意,这李副厂长事到临头,还不坦诚,看来得把他给撤了。